新交互时代:《黑镜》成为现实,这对市场有何影响?
作者:许云泽,来源:腾云
原标题:新交互重塑人类社会:从直播、AI算法、脑机接口说起
在以人工智能、场景互联、感官操控三个关键词来描绘的新互动时代下, 一切交互方式都在变化,新的交互方式螺旋上升、孕育和淘汰彼此, 然后无数次地在同一条被称为“后人类主义 ”的河流中汇合。
无论显学与否,“新互动”作为一个命题,已经以媒介革命的姿态先后进入了政治学叙事、经济学叙事、代际与进化论叙事。
媒介技术一意孤行地往前走,我们时代最优秀的头脑则正将技术的琐碎细节一个个落地;政治家寻找他的支持者,资本嗅出消费者每一个毛孔的欲求,景观的铺陈以一切方式打开个体,并在此基础上将人群分野。
以“联结”为最终奥义的新互动,正在由一般意义上的“施——介质——受”构成的单向链路,重新发散出“信息——媒介——实体”的以太逻辑网络。
我们很难在时间的坐标系中定义“新互动”的“新”和与之明确对应的那些“旧”;在大体可以人工智能、场景互联、感官操控三个关键领域的开拔来描绘的新互动时代下,一切交互方式都在变化,除了电脑和手机屏幕,用户将迎来更宽广的交互空间,人脸、自然语义、手势,甚至脑电波,都会成为新的交互手段,它们螺旋上升、孕育和淘汰彼此,然后无数次地在同一条被称之为“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的河流中汇合。
2002年,当弗朗西斯·福山写下《我们的后人类未来》时,讨论着寓言小说《美丽新世界》时,他对于信息技术的理解仍然一鳞半爪,而更难以预判生物识别和仿生学在当下发生的这一世纪大爆炸。
信息通过交互系统整合而成一套编码,编织了一个当代乃至于未来社会的想象,一个可以完全按照程序操作、也随时面临迭代和崩溃的系统;媒介和技术变得不再是人类个体与社群互动的工具、而成为个体的延伸,成为越来越具备有机物生命体征的“幻肢”,一个独立的实体,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

▲庞茂琨作品,《被直播的现场》,280*230cm,布面油画,2017。这位知名艺术家不仅让齐白石穿越时空进入了维拉斯凯兹的名画《宫娥》中,也让现代观众(包括他自己)置身于此,直播那场著名的宫廷肖像绘画现场。图片提供:北京民生现代博物馆
01、直播:经验复制 or 知识生产?
在当下讨论“新互动”,最显性的动因之一来自于“直播”的瞬间爆发。
当几百万人在线“逛故宫”,出版机构和文化学者的讲谈录以主播身份再造,全球博物馆最细致和丰富的历史切片通过直播信号直接抵达每个个体私享的屏幕,“空间”与“在场”被场景互联重新定义,人们为了获取知识所需跨越的那些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被莫比乌斯般地缩短,卢浮宫和莫高窟不再是东西方文明截面的历史跨度,而仅仅是一个直播间到另一个直播间的距离。

▲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名作《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及学者戴维·温伯格的英文原著《知识的边界》
知识的流散以口口相传、以纸书出版、以广播和电视信号、以数字化的代码呈现、最终走到直播形态,似乎打通并压缩了知识传播的整个历史,将data、message、knowledge归一,营造出新互动时代的口口相传。
手机屏幕像一个橱窗,展示着文学与艺术、历史与文明的画片,固定镜头的直白记载,解构了蒙太奇对影像的辩证与象征化处理,而观者与屏幕橱窗内的展示者之间短兵相接的互动,毫无门槛、随时可以介入的留言,将剧场艺术一千年以来的“第四堵墙”打破。
直播互动从网红经济的机械复制攀上知识经济的再造分发,从广告营销的算法推荐到公共教育的伺机而动,几乎仅需跨越知识阶层的一点点尊严的不适。
知识者不再需要建构传统意义上的文本,而仅仅使用“谈论”去触达本体,直播的互动重新激活了他们表达和授业的欲望。互动取代启蒙,也重塑了思考,我们将不是一个个孤独沉思的物种,而是通过各种符号标记、人工制品来进行思考的族群,词语、键盘、手机屏幕都成为我们思考的媒介。
新互动归根结底指向了知识的生产和分发方式的一万亿种可能性。
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知识的边界》中提出了一个类似麦克卢汉“媒介即知识”式的大胆论断,即“互联网本身并不拥有创造知识实体的要件,……知识不存在于书籍当中,也不存在于头脑之中,而是存在于网络本身”。
对于直播互动来说,能否发出新的断言,互动即知识?新互动是一场信息技术的工业革命,抑或是改变了我们处理知识方式的事实?
当我们识别海报上的二维码,进入一个个随时准备被向上划走的直播间,知识生产的优雅与神圣的迷信被祛魅,我们甚至不需要预备好书写和阅读的训练,就以消费者的上帝身份成为它所提供的丰富与过载的审判官。
一个严肃的讨论在于,直播知识,究竟是一种新的思想景观的生产,还是仅仅是文本经验的转码和复制?直播以展示者和观者的最即时和碎片化的互动所带来的“共构知识”,究竟是释放了大部分人记忆的存储从而使得群体走进更深的智慧的丛林,还是仅仅是对网络生产持极端乐观主义者幻想的文化生态模式?
迄今为止,我们并不能追认任何一场直播即时形成的文字、图像和声音的符码能够生成一个经典意义上的“文本”,并在此基础上诞生新的知识;它要么降维且压缩地转述了旧文本样态中的知识,要么呈现一种“次生口语文化(美国文化历史学家沃尔特·翁)”的光复,即文字稿的口语传播。
直播式交互——因其越来越大屏、直面镜头、短视频化——使得人群的聚集变得像古希腊市场(bazaar)那样熙熙攘攘、众生喧哗,而它是否真的像它所呈现的景象那样,隐喻了后人类时代对自由聚散、交谈对话、人与人互动的生命世界的渴望?

▲一个直播现场的后台。直播卖货成为当下热门风口,抛开对经济维度的讨论,这一形态亦已象征着互动以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形式触及消费,影响人的观看、购买和互动模式。
02、算法:人的去中心化 or 控制论
被大数据训练有素的算法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拔,意在构建关于人类全体的人工神经网络(ANN)的模型,我们的一切衣食住行、思想和情感的信息,在这个神经网络的各个末梢,都将不再是生命体征,而成为交互的不可或缺的元器组件;云端算法通过交互获取用户反馈,又将信息库用以更新完善交互所能触达的精确度和纵深度,从而去完成越来越精准的广告投放、产品营销和内容输出。
算法的持续且最快速的进化,与交互的革新在时间逻辑和因果逻辑上都存在极大程度的重叠。
新的产品设计和交互设计越来越便捷、直截了当、体验良好,就愈加得以通过商品图像的消费符号和象征兜售不必要的欲望,通过大众传媒和社交媒体这些社会控制的关键装置进行“全景式传播”,最终实现盛景资本主义(spectacular capitalism)对于人在身体、时间、行为和情感层面的统治。
英剧《黑镜》曾向人们预示过那样一种社会,人在交互设备的一端对另一端的商品召之即来时,人本身即已成为资本体系控制下的另一种商品存在,随时可被挥之即去。
旧算法的本质是机器学习。
三年前,打败柯洁的新版本的 AlphaGo 实现的一个能力进路方面的突破即在于,机器不需要学习人类已经学习过而形成的知识;它不再依靠某种先天的规则和程序,无需学习显性的知识,而只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践,根据与环境的交互中获得的奖励反馈,调整神经网络的行为策略的趋势,就可以逐渐获得特定的技能——更极致接近于人类自身的大脑和身体在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中习得技能经验的进路;DeepMind 就此在他们发表的论文中提出,这是一个没有人类知识(without human knowledge)的系统。
这的确是一个全新的系统。当马斯克宣布“脑后插管”黑科技首款产品发布之际,脑机融合的科学甚至绕过算法的机器学习的原始积累,直接从大量人脑细胞和神经元中捕获信息并将其无线发送到计算机以供分析。
人工智能领域八十年来的连接主义、符号主义和行为主义三大流派的历史论争就此预告终结,究竟是依靠数理逻辑,依靠仿生学、抑或是依靠感知-动作的控制系统,变得不再重要,标准化规模化拓扑化的“机器科学”收编了模糊而暧昧的“脑神经科学”,人的边界被打开,人类思想需要先转化为语言再通过键盘、鼠标等输入工具传入计算机的过程被省略,直接的人机交互使得从一台设备下载、存储、压缩、上传人类思想体系和认知系统至另一台设备成为可能,人类的肉身在人机互动界面的一端一点一点拼成一个半机器人。
至此,福柯在《词与物》中描述的那个人类知识的海滩经受着时间浪潮一次又一次的冲刷,以人为中心的知识结构和话语正在被系统的知识、非人的和物的知识慢慢取代,正在形成人被交互控制、交互胜于人之能动性的现象,甚至预示着以人的更大幅度的让渡和更轻易的被支配,去达至人机的新的平衡。
当“人即万物的尺度”被瓦解和悬置,我们是否能够突破肉身的局限性,以更好地与这个世界共存;而如果大脑成为了一台台 CPU,语言和沟通顿时变得多余,我们仍不能发展出与之对抗的社会力量,我们最后是否真的会失去选择和思想的自主权?

▲著名英剧《黑镜》第一季中的《你的全部人生经历》剧照。这一剧集揭示了一个祸福参半的未来场景——人可以通过人工智能一般的眼,拍摄、储存所见的一切,并可以随时回放,因而,所见就不仅仅是私人的记忆,也成为公共的大数据。
03、媒介:联结 or 规训?
是VR、AI、还是Tough Designer?是触控手柄、全息触屏、还是脑机融合?
新交互探索和开拔的终极奥义在于,如何使用一种越来越具身性(embodiment)的技术,在无需把机械装进肉身的前提之下,实现人与机器的连接和交互。
德勒兹曾经用“颅内电影”描述芯片植入大脑后产生的人机联结,而新互动甚至仅需屏幕和一切插件就可以实现非侵入式的连结,且通信速度更快,“带宽”更大,其在感官操控方向上的激进,使得无机世界全部“听令”于人变得可能。
后人类的观点认为,人的身体原来都是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因此,利用另外的假体来扩展或代替身体就变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它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安排和塑造人类,以便能够与智能机器严丝合缝地链接起来。
在后人类看来,肉身的属性存在与计算机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或者绝对的界限。通过知识图谱,可以帮助我们把杂乱无章的信息结构化,构建认知智能的基础,再结合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进入真正的认知智能时代。
屏幕诉诸视觉,最终诉诸其对感官的规训和控制,可穿戴设备既赋予了佩戴者以控制权,同时又拿走了控制权,手机开始告诉你应该和不应该吃什么,也将开始告诉你应该跑多长的路。它将介入你和你的身体之间,离间两者之间的关系。
可穿戴智能设备会让你物理上的自我以信息的形式出现在虚拟世界中,留下不可磨灭的数字印记,而那些信息的可操控方式将跟今天的其他任何信息毫无二致,可被复制和散播,到最后很可能会流传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方。
媒介修正着人类对自己身体的感知体验,既跟主观、思维活动有关,也与机器、代码、社群有关,它们处理的不仅是人类感官的延伸,而且要处理延伸的结果向内投射到情感结构及生命形式之中,从而改写着人之所以为人、以及人类社会之所以形成社会的方式。
互动的技术和叙事都会历经迭代,劣币和良币相互驱逐,旧有的媒介文本和评价机制攻击着彼此,以各个触点上微小的变量煽动体系的变化。
互动媒介越来越适应我们的身体,适应我们体内一套不需要通过训练就能自如显现的语言范畴,同时在另一个向度上,迫使我们身体的自然机制和经验建立更友好于互动媒介的新的规矩。
如果新互动的实践能让人工智能和感官操控设备从一种媒介实验真正成为一种模块产品,并设定其规模化的工业标准,到那时,我们将不得不做出决定: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到底想要多大的控制范围?或者换种说法:我们已经为放弃控制做好了什么样的准备?
04、新互动:建构社会 or 被社会建构?
法国技术哲学代表人物贝尔纳·斯蒂格勒曾对完全计算机化(absolutely computational)的资本主义时代和全球性的数据经济(worldwide data economy)论断道,没有哪个人类社会不是由一种技术体系构成,技术体系被包含着技术体系本身的变革的进化趋势所超越,这种变革必然调节了构成社会的其他系统;技术体系(TS)调整社会体系(SS),同时又被社会体系所调整。
斯蒂格勒对基于大数据的技术变革能够带来的哲学意义上的知识和历史文化的中断,印合了我们在第一部分对直播的思考,而另一方面,他同时提出了新技术变革将激活重建新知识、新行为、新文化以及新的超个体化循环,并在此之上重建新的社会体系。
新互动对产业互联网和在此背后人的生存和生产方式将造成何种意义上的影响?
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一切交互手段都以宣教机器和渠道的性质被囊括于阶ji斗争论题中,个人能否获取更多信息并不由交互的技术应用而定,仅仅取决于其在阶级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对新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一切媒介都在进一步强化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霸权;对经济学家来说,市场法则决定谁使用电脑向谁做广告;对韦伯主义者来说,新交互使社会进一步分化为各种亚系统并助长科层权力;对技术决定论者而言,新媒介互动则进一步证实机器广泛使用所带来的进步,机器减轻人类艰辛,使自然顺应人类愿望。

▲古希腊神话中的少年那喀索斯临水自照,却被水中的镜像美貌所吸引,因而爱上自己的倒影,最终憔悴而死。但在艺术家庞茂琨的笔下,那喀索斯戴上了VR眼镜,这一自恋的场景也因而有了不同的意味。摄影:阿改
当我们谈论着信息技术革命能否带来人和群体的新的洗牌、改轨人的流动通道时,我们很容易从互联网时代教育资源的分配方式获知,社会结构和权力运作似乎并未随更全新的媒介与交互方式的引入而根本改变,一切都是新环境下老问题的重演。
然而,这些问题必须被看作一种从事实到规律的认识论进化的一部分。理论的探究远未能跟上新互动爆炸式的增补,消费主义、景观主义的批判都已经无法触及这种增补的内核,而只重复着它们早期萌态时人类关于如何自处的忧虑。
可供全球连接的网络视频会议在疫情期间突然需求暴涨之后,有学者曾经重提鲍德里亚对人机一体模式的批判,而这些批判究竟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指向已经势不可挡的新交互的一切突进?
打破了空间在场的现实界限的场景互联激发了人对于诗和远方的欲望,更立体多维便捷到位的感官交互捕捉人在腠理间欲望的碎片给予即时满足,人机的体外联结读取着体内数据的微小的律动进行编码放大,唤醒人们对于更极致体验的欲求;在一个哲学的意义层面,究竟是人类社会的这些飘浮在空中的欲望被交互技术不断攫取,还是新交互开凿、驯化乃至于操控着人类因欲望而不断打散、洗牌、重组的社会构造?
技术在每一个历史文化转型的时期都有特殊的隐喻。交互技术至今为止的隐喻或许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社会性和功能性;前者包含了空间、部落、结构、社群,后者指向认知、感受、知识、智慧。
技术隐喻能否塑造技术的乌托邦,正如政治隐喻曾经尝试过塑造的政治的乌托邦那样?
新交互改变着人类交谈的方式、群聚的方式,向外重组着社会运行秩序、资本和权力新的通道、社会关系和权利的公平法则,也向内规训着人类情感的信念、自我意识和福祉的扩展。这就是资本的自由市场。而无论它即将和终将去向何方,后人类时代已经轰隆而来。
作者公众号:腾云(ID:tenyun700)
转载请在文章开头和结尾显眼处标注:作者、出处和链接。不按规范转载侵权必究。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授权事宜请联系作者本人,侵权必究。
本文禁止转载,侵权必究。
授权事宜请至数英微信公众号(ID: digitaling) 后台授权,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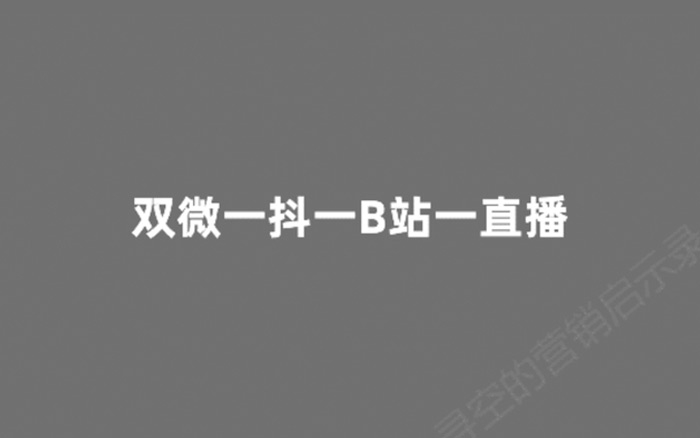





评论
评论
推荐评论
全部评论(1条)